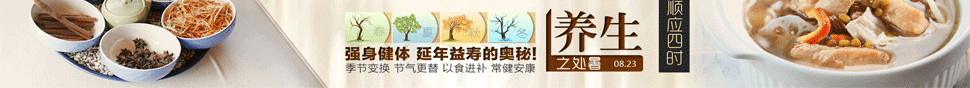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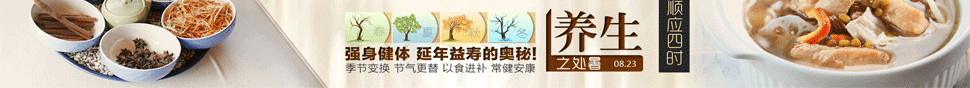
庄生晓梦迷蝴蝶,不知何为梦境何为自我;苏轼道“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感叹现实竟如水月般朦胧。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现实和梦境的关系,都充满了好奇,衍生出诸多的解读。
而作家鲁敏的最新作品《梦境收割者》,亦是沿袭了这一脉络,虽然写的是现实主义的故事,却又往往旁逸斜出,走入超现实的构境中。
以“梦境”为题,与书写“现实”,两者到底有怎样深刻的关联?梦究竟是我们“出世”的紧急出口,还是“入世”的必经之路?在鲁敏的写作序列中,还有哪些主题的嬗变值得探究?
三月底的“今晚三缺一”会员日活动,我们邀请到了编辑任柳,自媒体人王逅逅以及专栏作家、影评人杨时旸,来分享三位阅读鲁敏作品产生的感受与思考。
编辑任柳:
“气泡可以是脆弱,也可以是希望”
四月了,樱花也都开了。我看见有人说“你带着你亲爱的姑娘在樱花树下走过,那么这一趟人间很值得”,所以,我们也带着《梦境收割者》在樱花林里拍了一组新的视觉图。
我的同事在吹气球泡泡,乐得像个孩子一样。也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时间真的非常美好,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感受到。可能对于我们编辑来说,做书是传递,是信使,当然可能也装满了我们柴米油盐的日常当中降临的一些大事件。
不可否认,我们身上还隐藏着与古典浪漫主义相连的一些因素。我记得有个很浪漫的口号是“梦是唯一的现实”,但是,客观说,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亨利卢梭《梦》年
梦是一个很宽泛的词,它可以什么都不是,也可以什么都是,就像我发的这一幅亨利卢梭的《梦》,我在博物馆第一眼看到这幅画的感觉是:一个从没有去过热带雨林的画家,平时是一个海关公务员,靠着在动物园和植物园的观察,描述出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奇幻世界。
我自己做这本书的时候,很容易想到这幅画的隐喻。
我的朋友们问我:这个故事集明明写的是当下现实,写的是城市日常的故事,为什么要叫梦境?我说这是一个比喻,虚晃一枪。后来,鲁敏老师也写了一篇文章,说“生活,不过是梦境的别名”,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我和鲁敏老师就书名商量了很多次。鲁敏老师对文字有一种强烈的洁癖,而我自己也是一个很纠结的强迫症患者。这个书名,我们从“第零天”、“繁花十则”、故事文本当中那一篇《有梦乃肥》,包括“梦境的复述者”,直到现在定的更有力量感的“梦境收割者”。这个书名不仅呈现了一个写作者的形象,同时也呈现了一个阅读者的形象。
不管是从阅读还是写作的角度而言,我们所收割的是在日常当中看不到,但却会让人感觉到宁静或者疼痛的那一部分。
这本书的设计师汐和为这本书找到了最适合的样子。汐和最近也入围了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书籍设计提名。我最初想要找她来做书籍设计是因为我正好看到一本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
《怪诞故事集》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
李怡楠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可以文化年7月
汐和采用了矢量图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对作品的叙述风格和气质意象都有非常准确的表达。
在设计过程当中,我和汐和强调,虽然我们的题目有梦境,但是这本书不要做得很梦幻,也不要呈现得很柔和。我要有力量感、现代感和矛盾感。
之前我们和鲁敏老师商量,希望能够用图形来呈现这个书整体的一个封面。汐和就做了三稿,两稿是用插画,一幅是她画的矢量图。插画里的一稿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幅画。画作的原名叫做Farewell,作者目垂是央美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零零后。
Farewell目垂绘
我很感谢汐和能发现和关联到这么厉害的一个作品。我们和目垂沟通的时候发现,她真的是一位很坚持保持自己艺术感和神秘感的比较谨慎迂回的年轻人。她谈她的创作时说:我画的只有人本身。她的作品缄默而冷峻,绘画作品背后的深意难以断定难以言尽,却足够令人着迷。
这是不是我之前说的“梦境”,什么都可以不是,也什么都可以是?
封面设计汐和
而巨大绚烂内容丰富的缤纷气泡,它是希望,是脆弱,是从人与人之间的日常里蒸腾出的大的华丽的事件,是我们在这个轰然奔走的大时代里被书写下来的故事。它闪耀着被记录被讲述的光芒,但是它不可确信不可触及,它模棱两可,它须臾可能消失,在你阅读之前。
自媒体人王逅逅:
“尘世间有价值之物,尽是他人之梦”
《梦境收割者》这本书不是很难读,算是可以一口气读完的一本书。读这本书让我觉得,我像是一个小孩读一本大人的日记。
为什么说是大人的日记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它有很多忧伤而无可奈何的细节。人到成年的某一个时间段,突然觉得有一种被困在牢笼之中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小孩所不太能够体会的。其实《梦境收割者》这个书名,也有一种被囚禁,像韭菜一样被收割的意味。
读完这本书,我窥视到了另外一个成人有点无奈又充满自言自语的絮叨。这样的生活其实像在看伍迪艾伦的电影,感觉是一个人与自己的对话——即使每一个短篇小说的主角都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伍迪艾伦《安妮霍尔》剧照
我想分享一些这本书中打动我的句子:
导师的身影,像一粒小方糖,很快融化在咖啡般又香又苦的机场大厅,我挥了好久的手,一边咀嚼他道别前的话,像一个撤回键,把这整个中午她带给我的力量全部消弭了,或者这些年的力量本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这样的段落很打动我。作者把一个他者的身影比作融化在咖啡中的一粒糖。我自己也是在消费品行业工作,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境是可以通过一种商品表现出来的。这句话会让我脑中立即有一个场景——有一种又苦又甜的味道在我心中弥漫开来。
第二个想分享的段落在《有梦乃肥》里。这个短篇小说很有意思,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女人可以通过梦预知别人的未来,但是当她发现有这个需求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由于梦不够多,她就开始编造一些梦境。
她现在才隐隐约约有些明白,那些所谓的快活、才华或成功,大概总是误会叠加以及将错就错的集合体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开始编造梦境以达到别人的要求,这句话描写了女主角当时的心境,同时又折射了一种现在社会上大家对于自己的未来,对于抓不住的东西的虚妄的控制欲。
我非常喜欢最后一个故事,一个中年女老板和一个诗人之间微妙的感觉。鲁敏在这本书中写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一个特定的结果,很多故事也没有一个达到读者心理预期的结局,就是:哦,这个谁死了?故事的结局其实被埋藏在了它的情节里面,它的过程就是一个结局。
从字里行间看出,这个作者觉得尘世间我们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的梦。这个梦可能是一个美梦,也可能是一个噩梦。
这本书整体给我的感觉,还是像我刚开始所说的那样,像是一个小孩儿在看一个大人的日记本。这个小孩也许会向往这种大人的生活,也许就是充满着一种不确定性。但是这本书里是没有道德批判的,你读完了以后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也觉得没有好和不好之分。
我非常喜欢这种字里行间有点出世的态度。
专栏作家、影评人杨时旸:
“从琐碎生活中,窥见常人的秘密”
我只读过五本或六本鲁敏老师的作品。鲁敏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相比起她写作的数量,我读得不是很多。
作家鲁敏
鲁敏是一个七零后的作家。七零后作家有一个很独特的共同特点——他们从整体上来说都特别扎实,也特别踏实。他们在文坛上,包括商业包装上缺少一些噱头,但是反观他们自己的写作,无论是鲁敏还是和鲁敏同一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有自己特别坚定的方向,也有自己特别想努力开掘的深度。在这一点上,是特别值得尊敬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敏其实代表了一个当下中生代作家中实力派的典型面向。鲁敏可能不像之前更长一辈的作家,好像作品里天然就有某种宏大叙事,看起来有更庄重的经典性;也不像后来的九零后作家看起来那么肆意自由。但实际上,如果你去细读,会发现作品里有很多她努力通过文本本身,去探求精神溯源的东西。
说一下《梦境收割者》这本短篇小说集。我特别喜欢第一篇《火烧云》,这篇在整个集子里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存在。
《火烧云》这个故事,是一个要出家的居士和一个世俗的女人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和互相搅扰。这个莫名其妙的偶然改变了彼此的命运和想法。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两条线。总结起来说,无非就是上山和下山,也就是我们说的出世和入世。居士是一直想出世的,但是意外遇到了一个来自现实的扰乱,他开始应对这种扰乱,有一些坚持,有一些说不清的小小动摇,让他也反观自己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就在这种变化当中,他感知到了自己想上山出世这种想法中,一些纯粹和不纯粹的内容到底占了多大比例。
但是经过中间复杂的变化,原本在山上的人下山了,原本在山下的人永远地留在了山上。这故事中探讨的东西很微妙。你说关于信仰吗?也可以。你说关于世俗吗?也可以。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对于自我存在状态的拷问。这种状态到底是外在的要求,还是内在的要求?到底是一种表演性的需求,还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需求?很多时候,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在山下的;有很多人住在山下的时候,心里也可以是在山上的。这个故事的结尾也很奇妙,它有一种突然降临的悲怆感和神性,这种状态很迷人。
如果大家读过,可能就会注意到这个故事中没有名字。居士就是居士,女人就是女人,山下来的这些客人就是客人。这样的一种写法非常神奇,它和这个故事本身非常合拍。它有一些脱离世俗,又始终笼罩着神秘感。
除了鲁敏这篇文章里的神性书写,我也特别想聊聊鲁敏作品中的欲望叙事。其实《梦境收割者》中一些篇目也涉及到了关于欲望的书写。这种书写不是很明显,鲁敏和那些很直白地书写欲望的作家完全不一样。她很擅长写日常生活琐碎,但是突然甩出几笔,就把日常生活当中暗藏的那种欲望写了出来。
有的时候这种欲望写得非常深入和极端,甚至有某种意义上的扭曲,但是你会看到,原来鲁敏其实是一个拨开了所有日常生活的云雾,看见了生活和人心最深处的真相的作家。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鲁敏可能算是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极端写作的实验。看起来特别轻描淡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压抑的,每个人都可能触及的那些生活;但实际上,她揭开生活的表象后,写到底层的欲望时就特别有趣。
《荷尔蒙夜谈》
鲁敏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1月
她此前也出过另外一个集子,叫《荷尔蒙夜谈》,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三人二足》,用欲望的方式呈现一个犯罪的故事。可能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对于故事走向的解决方案,但更多时候,是想更自由地书写那些欲望。
我觉得她对欲望的书写,有的时候写的是现实,有的时候甚至写的是一种超现实。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写作方法。读鲁敏的作品读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在很多篇目当中都会出现,比如《梦境收割者》中的《在四十七楼喝酒》。
鲁敏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有过很多其他工作经验,比如在邮局工作,比如做过记者。她自己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在做那些看起来没这么有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大家的生活像蝼蚁一般,每天生活在一种特别琐碎的状态当中。但是她能看见这些普通人的琐碎生活深处的一些秘密。
这些秘密可能也是让她开始拿起笔写作的一个冲动。
可能是出于作家的艺术本能,鲁敏在一些作品中明显地有一种想去书写“逃离”主题的冲动,尤其是她的中后期作品,比如《梦境收割者》中的《球与枪》。
《球与枪》说的是一个男人莫名其妙卷入一个案子,然后那个监视器认为他是犯罪者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讨论身份替代和自我走失的故事。它处于现实和超现实之中的一个暧昧状态。
《奔月》
鲁敏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0月
鲁敏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奔月》,书里也有一个出走者,一个叫做小六的女人。这种从日常生活中的逃离,从她熟悉而厌倦的状态中的逃离,一直是鲁敏喜欢探讨的一个话题。在《梦境收割者》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个主题。
《梦境收割者》
鲁敏著
中信出版大方年1月
《梦境收割者》收录了小说家鲁敏近年全新创作的十则故事,指向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实。鲁敏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生活的情绪,用文字深入人性的幽微,直抵现实生活内部的创口,为我们在微茫的希望里,找回梦想,找回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