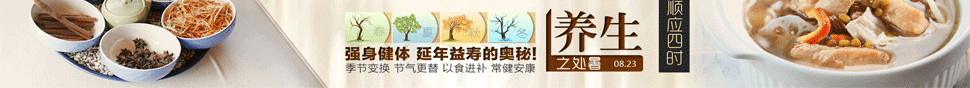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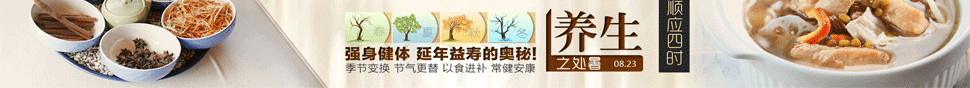
头条诗人年第6期《特区文学·诗》
沈苇沈苇,浙江人,生于一九六五年。著有诗集《沈苇诗选》、散文集《新疆词典》、评论集《正午的诗神》等二十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日、韩等十多种文字。曾获鲁迅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十月文学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金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李白诗歌奖提名奖等。
水上书(组诗)?沈苇◇三个傻子
第一个傻子住在生产队废弃的谷仓
他不知来自东边哪个县
更不知为何喜欢上了我们的村庄
白天,去镇上饮食店吃剩饭剩菜
黄昏时心满意足回到谷仓
有时喝了点酒,两眼放光
扯着嗓子唱:“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老太婆舍勿得那两块肉……”
然后就唱不下去了,他只会这两句
有时,提回半篮子烂水果
分送村里的孩子们
他死于除夕之夜好心人送的一条咸鱼
因为人缘好,公家为他买了棺材
全村男女老少为他送葬
第二个傻子是兔唇,远近闻名的“花痴”
屡屡被打得头破血流,屡屡还去追逐女人
远远看见兔唇,女人们就落荒而逃
躲进桑树林。她们最大的恐惧
除了蛇妖和传说中的吊死鬼
就是兔唇的袭击:出其不意地一摸
这一摸,在她们身上留下了
一辈子都无法洗去的耻辱
得手的片刻,他兴奋得手舞足蹈
兔唇里发出老鼠的“吱吱”叫声
第二个傻子最遭人厌弃、痛恨
但他崇拜第一个傻子
有一年发大水冲毁了桥梁
他嘴里叼了支冰棍游向对岸
去看望生病的外地来的傻子
游到河中央,冰棍化在了兔唇里
为此他哭了整整一天
第三个傻子,是我的堂叔
家里的老小,排列第八,名叫阿八
小时候送给了邻村一对不会生育的夫妇
他常回娘家,尤其在农忙季节
抢着替哥哥姐姐们干活
是干活的一把好手
在堂叔的脑海里
时间是一个令人头疼的概念
他常常分不清白天和夜晚
也分不清过去和未来
去年我见到他,头发全白了
我送他一包新疆葡萄干
一边客气地问候:
“叔,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哦,是后天。”他说
◇南浔之诗
雨停之后
河边菜馆里的杨梅酒
在继续
从水里打捞起来的
湿漉漉的话题
也在继续……
香樟叶柔软地铺了一地
仿佛春风里的欣然告别
一棵树可以是新的
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呢
当它抖去一身落叶,也卸下
前世恩怨积蓄的繁华碎片
一座名园有它的还魂记:
垂柳依依,拂过水面
如同死去小姐们寂寞的发丝
睡莲们继续睡着
在淤泥卡住的梦里
会有一种轮回升起、临近
待到盛夏,将重新谱写我
葱郁而孤独的恋情
雨停之后
有人在街上哼着越剧
一条狗跳过水洼,在桥头张望
雨水一度中止了生活
现在又恢复往日流动的韵律
像小镇一位平和的居民
我爱着菜市场里的气息和叫卖
像今生今世的留恋
雨滴仍在屠夫们的案板上跳跃……
◇奇墅湖畔
雨后,雾在山上溜达
到达云中的唐代名刹
湖面,马头墙的倒影
徽州民居的粉墙黛瓦
是一幅幅奇幻水墨
黑的凝重,白的惆怅
不闻梵音,但听多声部鸟鸣
把早晨变成一个巨型音箱
与人的胸腔、肺腑共鸣
绿荫中升起梓路寺的灰塔
仿佛出浴于微蓝湖水
它,正是寂静的今世本身
朋友们欣赏伟大盆景黄山去了
而我,徘徊在酒店与茅屋之间
穿过秧田、菜地和桑园
与三只戏水的麻鸭为伴
活到白头终得以发现
风景自有它的仁慈和好意
视游子、奔波者、背离者
为一块块失地,收复怀中
恰如挂一颗在体外的心
重新回到了体内
◇外地人
村里的老人说,那块地的地气太差
被土地爷施了魔咒
只能长出茅草、芦苇和苔藓
像无名的草木,这些来自黄河边的移民
被种植在那块贫瘠的地里
他们很少与本地人搭话、聊天
近亲结婚,或者从老家
娶回又丑又傻的女人
他们用一台老式收音机听戏剧
养了许多昼夜狂吠的狗
他们的中原口音,在吴侬软语中
变得微弱而零乱
他们的孩子从不与我们玩耍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村庄
心跳加快,像在躲避一种晦气
本地人的楼房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
他们仍住在低矮的茅屋里
用脸盆、木桶接着漏下的雨水
村庄里总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
游荡着秃子、跛子和哑巴
老人们说,这是因为那块地的地气太差
被土地爷施过魔咒的缘故
他们诅咒黄梅雨天,诅咒低产的稻田
当他们在水乡的小河边淘米、洗菜
一条泥泞大河从心头缓缓流过
……五十年后,外地人走了
带着儿孙,离开庄稼村
回到了黄河边。像一把生锈的铁钉
突然拔出原本不属于他们的门板
◇九家湾
十年前的泉水还在
喝上去像从前那么咸
出租屋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店铺和楼盘
村庄保留了一角荒滩
荨麻疯长,榆树孤单
一位逃学的巴郎子
蹲在我们的菜地上屙屎
十年中发生了什么?
你回到了南方
回到了小时候的村庄
种过地,养过长毛兔
重新捡起了老本行:油漆匠
期间自杀过三次
把自己弄成了残废
四十多岁,仍是光棍一条
今年终于有了好消息:
你自费出版了诗集《本土诗章》
阅读它时,我时常想起
你曾说过的一句话:
“因为悲伤,只能睡觉。”
但你不是嗜睡症患者
在那座消失的四合院里,你夜不成寐
为了完成一部梦想中的长篇
挥汗如雨,挑灯夜战
得意之时,竟旁若无人地
高声朗诵起来,惊动了你的邻居
几位刚下班的“小姐”,围了过来:
“阿锄,美玉般的心上人是谁呀?
阿锄,我就是那个乡下来的傻姑娘吧?
阿锄、阿锄,把我写进你的小说吧!
……”
十年过去了,就像漫不经心的时间
在乌鲁木齐郊外打了个盹
今天,我带着你的诗集去了九家湾
想找到你的“故居”
找到你过去的房东
想把《本土诗章》送他一本
郑重其事将它放到他手上
他不一定识字,但在翻书时
大概会一点点忆起你
我想看到他脸上的惊讶和笑容
但我什么也没找到
只找到从前的一块耕地
如今的一角荒滩
站在疯长的荨麻丛中
听微风细浪般涌动、吹过
鹡鸰贴着地面嗖嗖飞
两只布谷鸟,一唱一和
像一个词呼唤另一个词
我突然想告诉你:
远处的风和近处的风
正拨动大地的同一根心弦
远处的命和近处的命
本是一条命啊
◇饮者梁健
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将进酒》
你在天山深处挖过煤
在巴音布鲁克贩过羊皮
你是我的西域兄弟
我们在安吉挖笋、砍竹
在运河小镇、太湖渔家对饮
你是我的江南故友
曾经,你在沙漠里饮酒
饮着空空的杯子
曾经,你在雨中饮酒
杯子永远是满的
嗜酒如命者莫过于你
命,在酒里矫健、闪现
仿佛要再蒸馏一遍
倘若命有些落寞、芜杂
就用酒精来提炼、纯化
我送你一个蒙古酒囊
你立马如出征的欧亚战士
我约你在天山下畅饮
却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诺言
兄弟,我欠你一顿酒
封存在阴阳边界
开坛不会无期
酒是你的旗,你的盾
席间行云流水、叱咤江湖
如天空奔突青春、马头和烈焰
但我们已不再青春,不再昂扬
“青春不再又能怎样?”你说
“长寿或短命,如梦或如电。”
此为箴言。当凡人看破红尘
一个酒徒看破了杯中之物
你要实践,所谓友谊
就把最好一面展示给对方
把慷慨和热情无私交付
但,酒是你的云,你的雾
隐痛和哀伤,遮了一层纱幕
对于云雾之后的世界
时至今日,我仍所知甚少
也许,这就是你自导的剧
还有你作为一个杰出饮者
埋下的一个伏笔:
折腾自我胜于嘲讽人生
留下简明形象
也留下哑语和谜团
记得一年夏天在安吉
竹海中的天赋,人工湖
泄露的美,在一面明镜里
更新着蓝。我们如此珍爱
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的静谧
孔雀的叫声,像孤单的情郎
酒后的惆怅占据了长夜
夜雾里失踪的你,回来了
带着微醺,留下惊人预言:
“请允许竹林布置挽联,
允许大坝铺设神道,
允许我携带酒瓶和锄头,
允许我醉死水边,
在这个传说的酒香之坑。”
◇南屏
流水和石板桥的路
参天古樟指引七十二条小巷
一座心愿之乡的迷宫
是时间的固化,还是
空间化为一个过去时?
从弥散又密闭的幽暗中
从一只水缸、一张雕花木床
脱身,山峦和水田这般明媚
插秧女子,重复祖母们的残余动作
田埂上,缓缓走过一头老水牛
后面跟一个不急不躁的男人
白鹭、蝴蝶,扑闪眼前
这一刻,我毫不怀疑自己
正置身千年前的江南
归纳学意义的失效
——
评沈苇诗集《异乡人》
?赵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苇是很难被归纳的,我们或许可以笼统地将其称之为“抒情诗人”。“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往,但凡有点西部背景的人,都很喜欢强调诗歌中的雄浑、桀骜、苍凉。由于沈苇诗歌中所具有的西部的意象甚为广博,多年来,沈苇也被归纳为这一类诗人。
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西部想象去面对这一类诗歌,以满足自己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地理学的意义在文学的镜面中当然能够被照射,但那确实是一种虚像。我想,对于沈苇而言,这是一定意义上的误读。在我看来,沈苇一直是一位警觉性很高的抒情诗人。正像优秀的女诗人从不过于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沈苇也不愿意强调他是位“西部诗人”,而是“生活在西部的诗人”。曾几何时,“西部”的概念沦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陈词滥调。谈起西部,人们往往会陷入词语的误区,就像彭加木进入了罗布泊,深陷在那广袤的荒漠之中。最近,诗集《异乡人》的出版,为我们勾勒出了沈苇三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他的创作应该比西部更为广袤,因为他的镜像不仅是西部苍凉的微缩版本,他有着异于常人的诗歌虹膜,在那斑斓的诗歌里,有着对生命终极意义更为深远的追索。
在诗集推荐语中,耿占春和徐敬亚的评价显然更符合沈苇的诗学理念和诗歌风貌。耿占春说:“沈苇诗中所表现的个人体验的深度与范围,对社会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具有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的回应能力,使他能够把地方性经验转化为与时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诗学主题。他的‘诗歌地理学’由此变得宽广、深邃而无限。”徐敬亚则表示:“沈苇如同一条内陆河。他把现代汉诗和边关话语,与遥远的史诗遗传连接在一起。一种大气而精致的混血型诗意,正在他笔下形成。”
耿占春和徐敬亚更为精准地把握住了沈苇的诗歌脉络,让他的精神谱系更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沈苇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西域与江南,的确是差别很大的两个地域张力,自然、地貌、族群、历史、文化等层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几乎是地域的两极。我是差异性的受益者,也是分裂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地域分裂症’者,一边是江南,一边是西域,中间有鸿沟,有裂痕。我同时热爱这两个地方,但又不可能变成两个沈苇,各据一方。这就是我的困境和痛苦之一。唯有写作,唯有诗,能够有效治愈我的‘地域分裂症’。以前我提到过‘两个故乡’的概念,但现在,我常常感到江南与西域是同一个地方,或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为一个诗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地方,他面对的文学基本主题没有变,如时间、痛苦、死亡等。地域性对一个人的造就拥有与‘故乡’同等的源头般的力量,但在一位好的诗人那里,地域性只是虚晃一枪,他要揭示和表达的是被地域性掩盖的普遍人性和诗性正义。”
所以,沈苇早已抛开地域性的纠结,沈苇的警觉在于他对“诗性正义”不懈地追求。我想,这虽然也属于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当下却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一种姿态。在“下半身”“垃圾派”等口语诗派出现之后,虽然大家对他们的诗学主张嗤之以鼻,但潜移默化地,这些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审美。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些事件在欧美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布考斯基、垮掉派……他们对于基督教文明下的诗学解构,构成了欧美独特的风景线。同样的,口语运动挑战的是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当然,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交集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对“假道学”的某种冒犯。从诗学实践来讲,汉语新诗的“诗性正义”丧失得更彻底。因为,现代诗是跟古诗完全不同的领域,语言的风暴来得更为迅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苇坚持他的诗性正义,有可能陷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悖论。
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一文中如是说:“当诗歌想到它的自娱必须被看成是对一个充斥着不完美、痛苦和灾难的世界的某种冒犯,那么抒情诗的活力和逍遥,它对于自己的创作力的品尝,它那快乐的张力等等,也将受到威胁。”对此,沈苇在诗中一贯警惕。在未被收入到诗集《异乡人》的一些事件性写作的诗篇中,一直体现着他对公平、正义、人文主义的不懈追求。虽然,他也知道这只是诗歌的“无用之用”。“写作不是挺住,而是命运的眷顾。一首诗诞生了,世界没有什么改变,但或许,世界已经有所改变。因为,诗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抓住了虚无中的那么一点点光……”沈苇在《异乡人》的后记中如是说。
沈苇曾在诗歌中有这样的宣言:“你站在哪一边?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这是沈苇式诗性正义的总基调。在这次辑录的诗歌中,《在敬老院》是典型的一首。在诗篇中,沈苇说:“自己已提前留在了那里。”这种代入,又是诗性正义的一次获胜。这让我想起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在结尾,沈苇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但至少,他给敬老院的人带去了糖果、柑橘、牛奶,因为,桑塔格同时说:“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
我们送去糖果、柑橘、牛奶
也无法舒展他们脸上的漠然
虚弱,意味着无力向世界微笑
每天与绝望无助的人在一起
美女院长看上去那么忧伤
“来点歌舞,他们还是喜欢的。”
她轻声对我和阿拉提·阿斯木说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婆婆
盯着窗外雪花看,半天不动
身边的死亡消息,像飘忽而过的
雪花,都在她昏沉的意念之中
都在她一动不动的身体之外……
沿泥泞不堪的小路,离开郊外
这所简陋的维吾尔敬老院
谁也不说话,心里分明感到:
自己已提前留在了那里
在保持诗性正义的同时,沈苇的诗篇中一向拒绝学院派的高蹈,这是他对于表达的某种警惕。在沈苇数本诗集的开头,都收录着这首短诗—《一个地区》,可以说,从这首诗开始,沈苇确认了他的“诗学发声体系”。据说,这也是使沈苇能够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的重要作品。
中亚的太阳。玫瑰。火
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
那人傍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
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
关于这首诗,谢冕先生曾给出了如下评价:“我记得当初读到《一个地区》受到的感动,沈苇只用短短四行、三十多个字,写出了一个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撼的特异的地区,那辽阔,那无边的寂静。惊人的新鲜,惊人的绮丽。他对中亚风情的捕捉和概括如神来之笔。”
以《一个地区》为出发点,这样的写作成为了沈苇的“原乡”。在沈苇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的表达是丰富的,但从没有晦涩的诗篇。我想,在这点上,他和米沃什是一脉相承的。在《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一文中,米沃什这样说:“西方诗歌最近在主观性这条路上陷得太深了,以至于不再承认物体的本性。甚至似乎倡议所有的存在都是感觉,客观世界根本不存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一个人都可以说点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约束。但是禅宗诗人建议我们从松树了解松树,从竹子了解竹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为此,沈苇甚至向少数民族的民歌学习。比如《谎歌》一诗,就仿自哈萨克民谣。这些质地淳朴的诗歌,为他的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可能性。沈苇曾数度在酒酣之际,吟唱他拿手的新疆民歌。可以说,这些宝贵的民间艺术,不仅让他变得更加开阔,也融进了他诗歌的血液之中。
沈苇的警觉性还表现在他对于想象力的驾驭。阿甘本曾这样说:“诗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诗的发生/占位—因此也就既不在于文本也不在于读者(更不在于读者):它在于作者和读者在文本中借以把自身置入游戏,并在同时无限地从游戏中抽身而退的那个姿势。作者不过是他自己在作品—在作品中,他被置入游戏—的缺席的见证人或保证人;而读者也只能再次提供这种见证,是他自己按顺序也成为这场无穷无尽的游戏—他在其中玩着使自己消失的游戏—的保证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所谓的西部想象,也不过是阅读游戏的一个延伸。
在这方面,沈苇曾经在一篇名为《楼兰、西湖和希腊—关于诗歌的历史想象》中论述道:楼兰、西湖、海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历史想象这一视域去看,却具有某种互通性和互文性。世上有些地方、有些人事,属于人类想象力的势力范围。诗歌中的历史想象,与历史学、考古学截然不同,展开了人类语言和创造的另一维度。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拯救世界”,想象力也在拯救我们的世界。当逝去的人事、湮没的遗迹、模糊的远景再度回到我们眼前,世界依旧鲜活如初、充满生机,这是诗对记忆和遗忘的双重拯救,也是诗人能够创造的“心灵现实主义”。
他还曾向大家透露过一个秘密,在没有去楼兰之前,他曾为楼兰写过很多诗篇,包括收到《异乡人》里面的这首《楼兰美女》。他同时说,井上靖写过包括《楼兰》在内的很多中国题材小说,可是他从未真正到过那些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想象力对于诗人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无论是实现“诗性正义”或完成“混血写作”,沈苇一直在动用他的想象力。
近些年来,对于叙事的过分强调,正在动摇诗歌抒情的正殿。在这一方面,虽然他并不抗拒叙事,沈苇也始终保持着他一贯以来坚持的抒情性。据我所知,在正式写作诗歌之前,沈苇曾经写过数年的小说。乃至在后来,他也对小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西部》杂志八年的总编,他自然很清晰诗歌和小说的分界线,这在他收录《异乡人》最末尾的诗篇中可见一斑。雅克·朗西埃在《审美无意识》一书中这样写道:“于是,关于诗的整个思想体制拒绝了俄狄浦斯的剧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俄狄浦斯的剧情,在摒弃了艺术思想的再现体制之后,只能接受一个特殊状态。艺术思想的再现体制意味着某种思想观念:作为行动的思想给自己增加一个消极因素。这就是我说的审美革命:可见与可说、知识与行为、主动与被动之间的有序关系的终结。”对于沈苇来说,原来的故乡已死去。正如湖州乡贤孟郊的《游子吟》一样,在诗歌中站立的故乡,似乎永远是母亲的形象,这成为了乡愁诗歌的正典。如果说家乡带有某种“父性”的话,那么沈苇在诗歌中亲自完成了“弑父”。
为了完成它,沈苇再次动用了抒情的力量。在诗集末尾的组诗《还乡》中,沈苇用这样的句子宣告了“老故乡”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苇永远是一个“异乡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沈苇呢?
回到村里,一百年的老宅已拆
竹园消失,片瓦全无
幸亏,游子还有一具身体可往
简介赵俊,青年诗人。现任上海雅众文化诗歌编辑;编辑“雅众诗丛”;主持《花城》《世界文学》“翻译家档案”栏目;在《晶报深港书评》开设专栏。曾在《诗刊》《花城》《星星》《扬子江》《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中西诗歌》等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莫干少年,在南方》。
END关于我们
主管主办: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深圳市特区文学杂志社
顾问:
谢冕吴思敬舒婷欧阳江河张清华
编委:
唐晓渡王家新杨克树才娜夜海男汪剑钊卢卫平
社长/总编辑:朱铁军
副总编辑:宝蘭
主编:宝蘭
副主编:三色堇
编辑部主任:林栖
责任编辑:大枪颜久念
美术编辑:卢天豹
封面设计:刘菁
联系我们
国内统一刊号
CN44-/l
国际标准刊号
lSSN-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
港澳海外总经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46-
国外发行代号:BM-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深圳市报刊发行局
邮购处:深圳市特区文学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jiupinglana.com/jpljg/896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