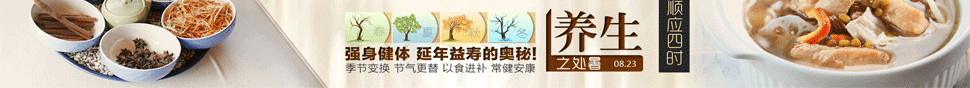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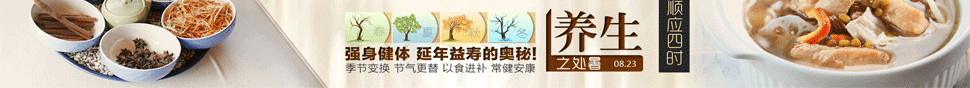
《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一对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大陆上因战乱而相遇,也因战乱而离散;两人虽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互不知情,私心苦恋四十年后才又相见,时已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且濒临病终。
《桃花源》是一出古装喜剧。戏里的武陵人「老陶」不育,妻子「春花」跟「袁老板」私通,老陶无奈出走,溯河而上发现了桃花林。度过一段纯真到近乎梦幻的时光后,他回到武陵,发现已往男欢女爱的春花与袁老板已再度陷入现实的纠葛和怨怼之中,并没有过成幸福美满的理想生活。
这两出戏在同一个剧场里争着排练,互相干扰,彼此打断,却阴错阳差凑成了一出往来引申、完美交错的戏剧。正如刘光能先生所评:「两出戏各有正反相背的两面,两剧彼此又恰恰正反相背。」如此精缜的安排,巧妙的构思,以及对当代中国人处境的同情与关照,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又如何成为台湾剧场活动的转折点?导演赖声川如是说──
01《暗恋桃花源》出现的时机我回国后导的头两出戏是艺术学院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及兰陵剧坊的《摘星》,我不去默认任何结构,在没有任何压力下发展,形式完全由内容所带动;《摘星》之成形尤其像音乐与诗的原理,而非戏剧。一些批评的反应是,即兴非常有意思,但是不是只能做片段的东西?于是我在艺术学院的下一出戏,就以即兴方式创作了传统观念中的完整作品──《过客》。
业余演员从事即兴排演,需要掌握三样条件:「我是谁?」「我在戏中的全盘状况应如何?」「我此刻面临的状况是什么?」就能进行发展。而专业演员还可以多出第三只眼睛来看自己。成立表演工作坊的第一出戏《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和李立群、李国修的合作便是如此。
我在《摘星》时认识李立群,他每天来看我们排戏,大风衣里面罩着秀服,有时候中间跑去做个秀又回来继续看。那时他不太讲话,很严肃。「相声」这个题材本来想找顾宝明、金士杰,但金士杰正好要到纽约游学,于是找上立群。他为了排《那一夜》,秀都不做了。
《那一夜》是喜剧体裁,即兴起来更难,要装包袱、抖包,还要有「第三只眼」在一边看包袱的发展。可以说有一个公式,但在即兴时还要套进公式,那就比较难。
一开始觉得《那一夜》必然是小众的东西,没想到会变成大众的狂热。我想,相声大概死了,现在谁会去关心相声?大概和关心平剧的人差不多。没想到还在巡回的时候,盗版录音带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叫「李国修、李立群大爆笑」,正版根本来不及供货。
一个剧团的成败,单靠一个成功不够,能不能维持下去?《暗恋桃花源》的压力很大。结果它比《那一夜》更成功。表演工作坊的基础,是靠《暗》剧打下来的。
《暗》剧之前,我在艺术学院导演的《变奏巴哈》,便已先定妥架构,再让片段从中生长。生长过程里,架构也会跟着变化。我开始不玩那么自由的发展,而给自己更严格的限制。
02主要灵感:台湾的混乱环境《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形式其实是陈玉慧导演的《谢微笑》在艺术馆彩排的经验所引发的。那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当时的台湾剧场完全没有管理可言,也没有对剧场的尊重──晚会、音乐会、毕业典礼都往里面乱塞。订好一个场地时,管理单位没人想到你还要装台、调灯、技术排练,随时会中间给你插个演讲活动。这情形直到两年前还发生过。
《谢微笑》下午彩排,晚上首演,中间两个小时就被安插了一场毕业典礼。但是彩排根本还没完,小学生已经坐在台下了,另一边钢琴、讲桌都等着要搬上台。这反映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如果说剧场管理不得其法,都已经讲得太深入了──根本是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做剧场的在干嘛。
03悲到极限与喜到极限我在柏克莱写论文时对希腊悲剧及日本能剧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古代希腊人看了三部悲剧之后,还要再看一个羊人剧Satyrplay才算完成?流传下来的剧本,有的只有悲剧,有的只剩羊人剧,都不完整。但深入研究便可发现,羊人剧多半是在讽刺前面三个悲剧。希腊悲剧本身境界就高,加上这个就更高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乃一动作之模拟,最后达到一恐惧、怜悯的净化效果。既已如此,加个喜剧算什么?我认为,当情感激烈到一个程度,再用另一个方式来嘲讽这种激烈,更能达到净化的目的,产生更高的境界。
希腊「悲剧」与「羊人剧」的关系如此,日本「能」剧和「狂言」之间亦然。能剧最是严肃、哲理、深沉,道尽万事无常,那么多鬼魂执着于世间那么激烈的事情上。然而却在上、下半场中间,演出一则狂言,大多直接讽刺戏的本身。日本人的喜感不像西方人那么发达,因而狂言可以说是用一比较通俗的方式,穿插着笑料向观众解释前面发生的事。倘有人看不懂上半场剧情,也可以藉此增加了解。
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悲剧里都有喜剧成分,那已是再进一步发展的戏剧形式,从纯粹的宗教,再加上民间的、文艺复兴的种种复杂元素。我感兴趣的还是像希腊悲剧、日本能剧这类较纯的戏剧形式。我一向认为悲剧、喜剧绝非相反词,而是一体之两面。悲到极限与喜到极限,人的脸部表情会是一样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却达到同样的结果:一样的忘我。「净化」便产生在这种忘我的情境中。
我一直想,把悲、喜剧同时放在舞台上会怎样?台湾剧场的现状正好提供了我描述的对象。
04用意大利艺术喜剧编排陶渊明的「假冒报导文学」《暗恋》部分的题材我摆在心里很久了。我大舅和我很亲近,医生曾宣布他得了癌症,只有三个月好活了(事实上他一直活到现在)。我二、三舅都在大陆,民国七十三年三舅可以到美国和大舅相会,那时他们在想,这是不是最后一面?非常通俗却非常真实。
用很不敬、讽刺的方式来改编桃花源记,也是长久以来想做的事。真正动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人人向往的桃花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个大问题。找出陶渊明的原文,真没什么线索,是个很正常的地方,只不过里面的人不知道历史,如此而已。对我来说这是个莫大的启示。陶渊明很高明,没像西方人那样尽力摹写一个如何如何的香格里拉。武陵人来到的桃花源就是耕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和中国任何一个乡下地方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有一片漂亮的桃花林。唯一的不同便是这些人「避秦时乱……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阵叹息,请这人吃饭。这是当年的政治批评。中共的旅游部门前几年还咬定在四川酉阳找到了真正的桃花源!陶渊明厉害之处就在于这根本是虚构的,他用报导文学的笔调来写寓言。看的人也知道他在假冒,他的写法也是要让人看出他在假冒,并且玩到底:最后还冒出一个「南阳刘子骥」──连人名都有了──想到有这地方,很高兴,就去找,却「寻病终」,陶渊明的句点下在这里。任何人中学都会读到这一课。在我们的求学过程中,这是满特别的一篇文章,悬在那儿,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可是大家都爱念。
排《桃花源》一开始便受「意大利艺术喜剧」的影响。这种传统和即兴创作很不一样,但我想玩玩看。排戏时我们试着玩各种书上记载的标准状况。例如:有一个聪明佣人和笨主人,主人处罚佣人,边打边数「一、二、三……」打一打就忘记刚才数到哪了,想想又从「二、三、四……」开始打起,打着打着又胡涂了。「打到哪儿了?」「到八。」佣人说。主人想想,不对,又从「二、三……」开始打。
另一个例子:两个骗子想混一顿晚饭吃。饭已经在桌上准备好了,两个人跑进来,表现得惊慌失措。主人好奇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将主人带到窗边,向外指指点点,另一个背着他们到桌前开始猛吃,吃饱了再交班。最后对主人说,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那就算了!两个人就走了。
慢慢地我们发展出自己的东西,像袁老板送棉被给春花和老陶那一段。戏中那个老陶永远打不开的酒瓶也是。我设定的状况很简单:你们三个喝酒,让老陶永远喝不到。演员自己会想办法做到,最后发展得十分精致。
拍电影时加了一些段落,将意大利艺术喜剧的精神发挥到荒谬无比的地步。比如老陶在桃花源和白袍男女一起生活。我们在武陵陶家已经玩过一床棉被上面有三个头的把戏,这里便玩棉被底下的脚。老陶看着白袍男女在晾被单,两人在被单后的剪影居然脚缠在一起,站着就胡搞起来,还一下一下猛撞着被单。一掀开,才发现两人原来在使劲扭一件床单。这是我们现场发展出来的。
棉被、喝酒都发展得很快,有些东西则需要慢慢发展。像袁老板去拜访春花、老陶,我希望他们想谈一件事,但怎么都谈不清楚。老陶形容「像月亮赤裸裸地照在光溜溜的大地上」,后来又说「在这一段长时间的光阴里」,袁老板指正他「『时间』就是『光阴』!」完全是非语言逻辑所能表达的东西。这些在电影中拿掉了。好玩,但拿掉也不可惜。
05感伤的喜剧……开罗紫玫瑰我的作品中一直有「拼贴」的概念,其实剧场本身就是拼贴的艺术。《桃花源》有许多华丽的东西,不断掉下来,掉下来,落在《暗恋》当中,《暗恋》的感觉、视觉、内容、思想,都是这些东西。
干扰,也是创作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动力,怎样让它推动戏剧?这出戏里有这个干扰、那个干扰,每次干扰都不太一样。《暗恋》中的导演会造成干扰,演员自己会造成干扰,外界也会造成干扰。这是有关干扰的一出戏。
要用《暗恋》的两岸故事来讲人对桃花源的向往,还是用《桃花源》来谈现在政治、人情的状况?都不容易说明白,两者也都不对。一定要两边加起来意义才完整。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暗恋》不是一个伟大的戏,《桃花源》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喜剧。从来没人问过《暗恋》怎么这么短?只有三场戏。前一届艺术学院的毕业制作就将这三场戏单独抽出来演,效果很好,令人难忘。但戏里我们一直暗示《暗恋》不止三场戏,还有一些你没有看到的。电影里我加了一景,应该换台北病房的景时,医院,十张病床一字排开。张叔平的设计十分精采,医院的味道。我安排云之凡刚好走过去,戏中的导演看傻了。景很亮、发光。导演痴望了一会,才开口要求换到正确的景。这只有电影能做到,舞台上不可能为了一个效果,就搬上十张病床。时间根本来不及。
《桃花源》很怪,一出喜剧闹得不可收拾,最后却是那么伤感。
《桃花源》的意念和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很接近。一九八五年我和杜可风一起在巴黎的一家中国式戏院看的这部电影。电影里,男主角从银幕上走下来,观众还坐在那里等他,结果他走了,戏演不下去了,他跑去请米亚.法萝吃饭,付钱时掏的却是道具钞票。两人坐上车,米亚.法萝叫他启动,他说:「在电影里车子自己会开的。」在经济大恐慌的年代,社会萧条,家庭也不美满,唯一的出路就是去看电影,作为一种逃避──这一点很像《暗恋桃花源》。最后男主角被骗回银幕,米亚.法萝回到戏院,看佛雷和琴姐的歌舞片。刚开始时,她没有在看,后来渐渐被银幕上的画面吸引住了,最后出现了与开场她看电影看得入迷的同样一个微笑。
06创作一出舞台剧我们正式的排演开始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最初是一周三天,到十二月中旬变得比较密集,直到次年三月的台北首演。排戏的地点到过秀秀(刘静敏)家、阳明山我家,还有兰陵、云门的排练场。其中以阳明山的日子最值得怀念。那年下雪,我们在壁炉边烤火。大家到了就开始煮饭、烤面包、准备晚饭,吃完饭讨论一阵子,再排戏。
开始的几次所有人都到了,初步探索之后,就分开排。然而排《暗恋》时《桃花源》的人经常会到,反之亦然。大家共同关心戏的发展,像一朵花,是个有机体一般。
整个结构很早就出现了。我和金士杰一起去找家里一位姓杨的长辈,当时是台北商专校长辈,东北吉林人。问了他不少事,建立了江滨柳的雏形──「一九二五年生,四○年离家赴成都,四三年入大学,四四年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四七年抗战胜利,无家可归,在上海杂志社做翻译工作,四八年认识云之凡,八五年得肺癌。」之后金士杰就可以带着这个球跑了。
《桃花源》一直发展得很辛苦,卡在进入桃花源之后。那是个什么地方、什么状况?我们甚至停下来讨论这些问题。原本计划由陈玉慧、苏姻玲、游安顺饰演进入桃花源后的三个角色,结果这三个演员常常不能到,正好提供了机会,让观念豁然贯通──桃花源中的白袍男女,就是春花和袁老板两人,没有任何其他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深富启示。即兴创作的妙处便在于,参与得越多,发展的东西越容易成为结构中的要项;经常不出现,最后可能就不需要出现了。桃花源成形之后,陈玉慧便成了陌生女子,游安顺成了个二楞子。这都是原来草稿中没有的。这是出席、缺席造成的结果,反而更理想。
参与多少就得到多少,这是即兴创作的必然现象。因为整体正在生长,一切都在互动,角色自然而然地会充实、膨胀。
陈玉慧本来就常做出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她起床泡好一杯茶,到排练场时那杯茶还在手上。显然是坐了公交车来的,她自己却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她的经典故事。
即兴创作是「有什么人就做什么事」。《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过客》都是因人成戏。《暗》剧起码有一堆预设角色,就特别要费心选角,去想象某个人的特质可能会「带着这球往哪里跑」──把戏带往何方?
原本设想由胡茵梦演云之凡,邓安宁演医生,杨丽音演江太太。至于金士杰的江滨柳、李立群的老陶、顾宝明的袁老板则自始未变。最难找的是春花,弹性很大,那时找过汪其楣跟马汀尼,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有些距离,都拒绝了。最后找到秀秀,她刚回国,演过金士杰的《今生今世》,两剧角色颇类似,但她那时满脑子果托夫斯基的概念,不知道能不能适应我们这种方式。她很痛苦、矛盾,又放不开,在宝明、立群两个快手中间,玩得很辛苦。但她毕竟有演过《荷珠新配》的底子,最终塑造了一个带有纯真朴实气息的春花,和第二版的乃筝很不一样。
07打破禁忌,完成潜意识的愿望《暗恋桃花源》演出时只能以「盛况」来形容。尤其是两剧团同台排演的那一段,前台服务人员一看时间到了都会进场一再重看,我个人觉得那段是个「经典」。立群和宝明都看到艺术馆第一排有位观众,当场就笑得从椅子翻下来滚到地毯上。这次在美国旧金山演到《暗恋》最后一场,江滨柳和云之凡重逢时,观众席里不知从何处传来一盒卫生纸,很自然地每个人都抽了一张又传下去了。
我认为这出戏这么受欢迎,很多因素是由于完全符合了台湾经验,就是乱、干扰,从这中间钻出了一个秩序来,满足了众人潜意识的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是我们的共同经历,将它转变成剧场中的错误,让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调了。尤其是两戏同台对峙那一段,触到了我们的潜意识。生活本身就是那么乱,台湾社会的步调又是那么快,然而身在其中的人自有一种乱中的秩序。看这出戏的经验统一了观者很多生活中的乱象,又涉及最敏感的时事──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首演时,这话题还是禁忌。那时我们每推出新戏,都小心计算过禁忌的界限在哪里,而我们要超越多少。有的人不管界限,自己做自己的,或是故意破坏界限,让当权者完全没有面子,许多当时的小剧场便是如此。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其中舜天啸说到他前世临终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官员来看时,我相当紧张,还故意把他拉到场外聊天,听到场内哗然大笑,知道那句话说过了,才放下心:过关了。那时剧本审查制度还没废除,我们都另行伪造送审本,还故意写些话去让他们删。看那些剧本你会笑死,都有光明的结局。其实政府也知道那假剧本不能约束你上台讲什么,也知道即兴创作不可能有一个真剧本──我们自己都没有。
《暗》剧的含意在当时是很严重的,很容易会被批注成:你还可以想大陆啊?其实江太太这角色就是重要的象征──你眼前这人都不管,还管大陆那个!那个又是什么?就算见了面还不知道有什么话可以讲。这戏谈的东西满全面的,也的确雅俗共赏,比《那一夜》成熟许多,也让我们看到即兴创作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暗恋桃花源》的演出,将台湾剧场的格局打开了,使戏剧演出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正常活动,不只是少数人的前卫艺术。之后许多小剧场也开始绽露头角。台湾的现代剧场之路上,兰陵剧坊的《荷珠新配》可说放了一把野火,赖声川的第一出戏《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只有少数人看到,但影响很大。《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造成一热烈的文化现象,但仅是一股风潮;直到《暗恋桃花源》出现,巩固了已往的成果,也稳定了「表演工作坊」的格局。那时吸引了不少中学生进剧场,成了忠实的观众群。如今这些人都已大学毕业、入社会工作,对整个社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END(本文转载自鸿鸿、月惠合编的《我暗恋的桃花源》,作者赖声川,图片来源于网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